强奸修女这种极端题材起初让人难以接受乃至相信,对宗教清规将人性的自我束缚造成的信仰崩溃与伤痕放大更是挺有微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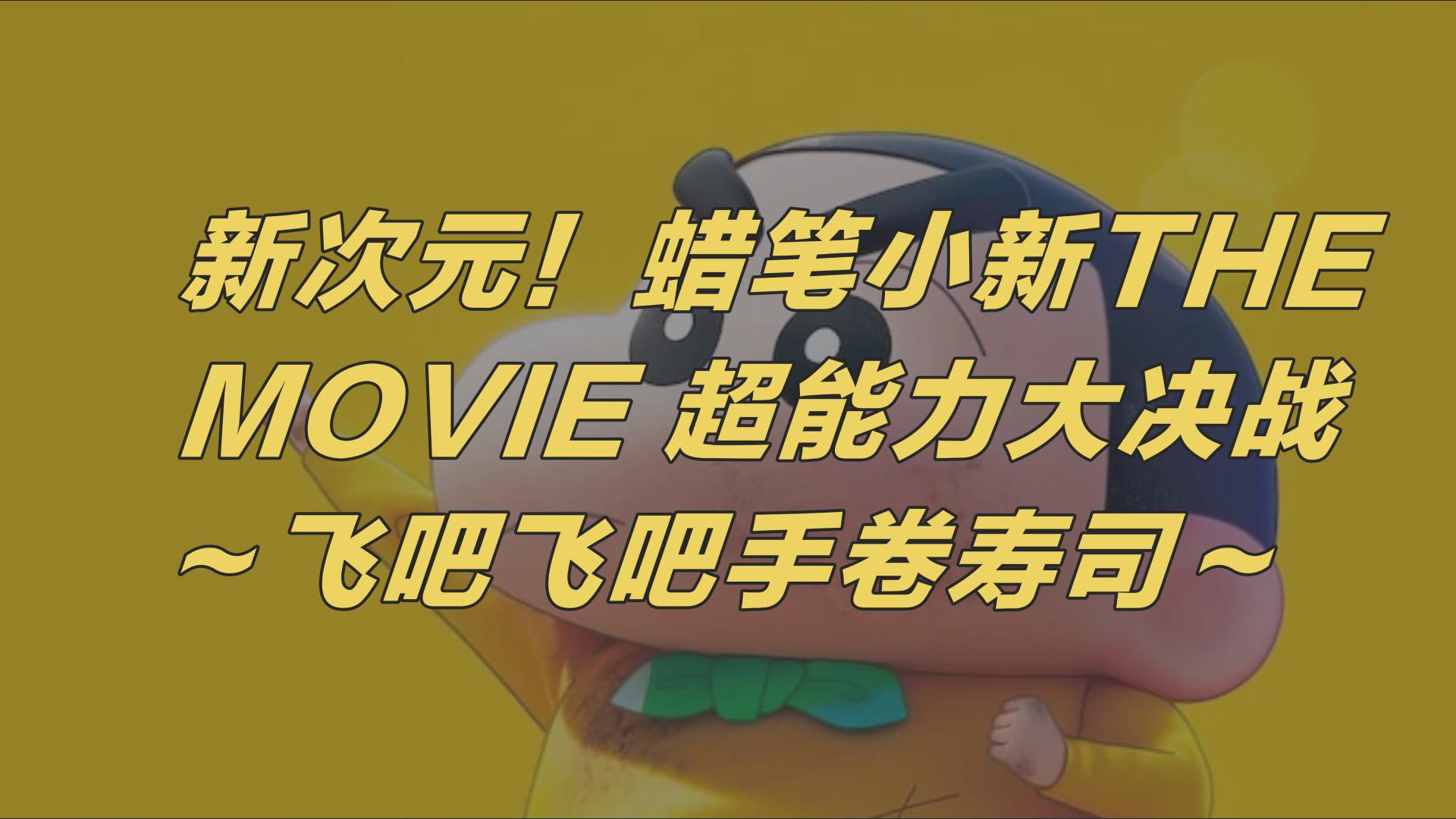 但必须考虑到修女们首先依然是人,是女人,是比俗世身心更单纯更讲信念的人,对于没能保护她们遭到初次欺凌的伤害,怎能忍心对她们再进行二次伤害呢?影片一个较高的思考层面其实在于如何对待受害者避免其遭到二次伤害.
但必须考虑到修女们首先依然是人,是女人,是比俗世身心更单纯更讲信念的人,对于没能保护她们遭到初次欺凌的伤害,怎能忍心对她们再进行二次伤害呢?影片一个较高的思考层面其实在于如何对待受害者避免其遭到二次伤害. 当无辜的她们遭到了暴力欺凌的野蛮残忍,如果再对她们母爱的无私给予摧残,那就是在残忍的基础上更加了一层卑劣无耻.
当无辜的她们遭到了暴力欺凌的野蛮残忍,如果再对她们母爱的无私给予摧残,那就是在残忍的基础上更加了一层卑劣无耻. 正是用爱来回应无辜的下一代,而不是用“这些杂种”来获得“我不是最惨的”的卑劣优越感,人类才能缝合伤痛,不再延续漠视生命尊严的历史循环.
正是用爱来回应无辜的下一代,而不是用“这些杂种”来获得“我不是最惨的”的卑劣优越感,人类才能缝合伤痛,不再延续漠视生命尊严的历史循环. 当然,如修道院长这样已经梅毒缠身,还先作恶再忏悔负罪的假惺惺实在不值得同情,罪恶已然作下,生命不可挽回,若真有上帝,会让她只受这种自封的诅咒?
当然,如修道院长这样已经梅毒缠身,还先作恶再忏悔负罪的假惺惺实在不值得同情,罪恶已然作下,生命不可挽回,若真有上帝,会让她只受这种自封的诅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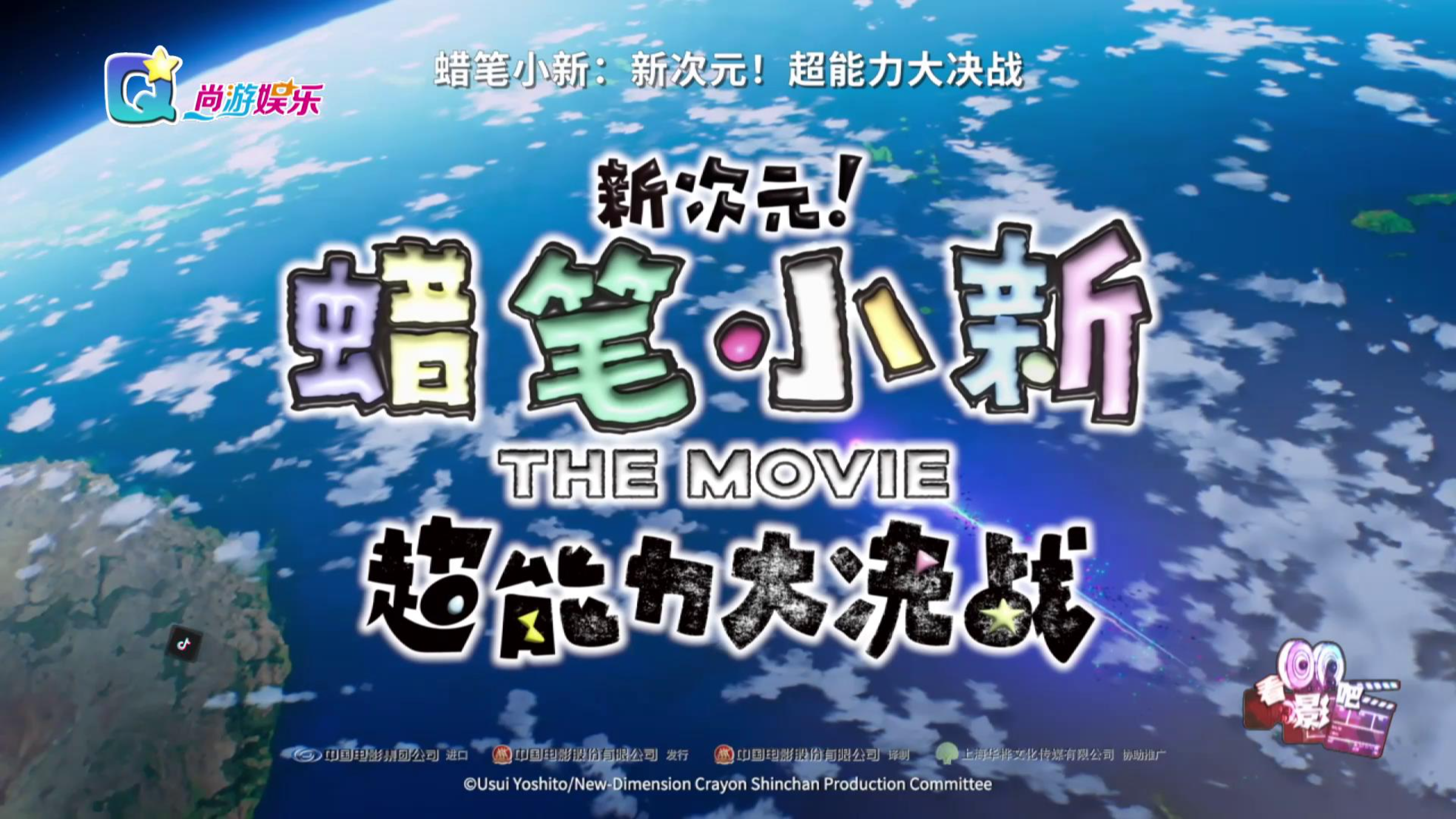 7/10.
7/10. 导演将画布拍下来和城市的实景叠印在一起,使画面具有油画般的颗粒质感,尽管这种尝试仅在开头等处出现极少,但成功表现了画家就活在灵感中,营造了惆怅的情绪,为后来他浪漫又不切实际的追寻提供了心理依据.
导演将画布拍下来和城市的实景叠印在一起,使画面具有油画般的颗粒质感,尽管这种尝试仅在开头等处出现极少,但成功表现了画家就活在灵感中,营造了惆怅的情绪,为后来他浪漫又不切实际的追寻提供了心理依据. 叙事的造梦和反讽机制可能影响到[开罗的紫玫瑰],情节设置充满虚幻性又用细节力证珍妮的真实存在,譬如画家走访了马戏团的老员工、修道院的修女,无一例外说珍妮确有其人,画家也确实在同一日期赶来灯塔,目睹了海啸冲走珍妮,画家从海中遇救后史彼妮小姐还在岸边捡到了珍妮的围巾,结尾瞻仰者们对珍妮的画像议论纷纷:安详的面容,忧郁的大眼睛,真.
叙事的造梦和反讽机制可能影响到[开罗的紫玫瑰],情节设置充满虚幻性又用细节力证珍妮的真实存在,譬如画家走访了马戏团的老员工、修道院的修女,无一例外说珍妮确有其人,画家也确实在同一日期赶来灯塔,目睹了海啸冲走珍妮,画家从海中遇救后史彼妮小姐还在岸边捡到了珍妮的围巾,结尾瞻仰者们对珍妮的画像议论纷纷:安详的面容,忧郁的大眼睛,真. 画家其实借他者构筑自我形象,他不愿出卖灵魂画裸体维系生计,但内心真实的情感无处表达,被评论道花的绘画毫无生气,珍妮是萧条时期的自我藉慰,就是那稍纵即逝的灵感.
画家其实借他者构筑自我形象,他不愿出卖灵魂画裸体维系生计,但内心真实的情感无处表达,被评论道花的绘画毫无生气,珍妮是萧条时期的自我藉慰,就是那稍纵即逝的灵感.